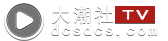世界500强正大集团谢国民资深董事长畅谈家族史(二)
▼
1939年我出生在位于曼谷旧市街的唐人街,这个被称作耀华力路的街区,如今已变成有名的旅游去处。父亲在昭拍耶河边开了家“正大庄”种子店,店铺与码头仅相隔200来米。
那个时代没有汽车,昭拍耶河是曼谷经济的大动脉。商人和农民坐着船在河上穿梭往来。码头旁边有个自由市场,有很多卖农产品的农民,熙熙攘攘。卖完农产品,他们总会到正大庄买些菜种回家。
父亲早在潮州老家成婚,生意兴隆后便把母亲从潮州接了过来。在与种子店隔街相望的地方,父亲又开设了一个总部。一楼是办公室和仓库,二楼、三楼用于居住,屋顶则用来晾晒种子。
我出生在三楼,三叔谢少飞一家住二楼。家人不准我靠近办公室,只准我在后院玩耍。一楼摆放着很多装着种子的铁罐。种子比较娇气,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密封在铁罐里的种子可以得到妥善的保管。
办公室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位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坎贝尔,负责翻译国外信件和撰写贸易文书。他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比父亲的还大,房间里设有会客厅。办公室里还有会说英语的泰国人。
时至今日,正大庄周边的风景跟我小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作为卜蜂集团的一员,正大种子店仍在继续拓展业务。我出生的那座楼现在仍是菜种行的总部,总部对面的店铺也一直在卖菜种。大哥谢正民和二哥谢大民创办饲料业时租赁的那家店铺也依旧在种子店旁边。

(谢国民先生出生的地方,现在是正大种子业务总部)
马路上看不到汽车,非常安静。从中国来的潮州人很多在这里开潮州菜馆或茶叶店,出售中国产品。街上挂满的店铺牌子也跟从前一样,都是传统的中文商号,刻着汉字。置身曼谷唐人街就仿佛置身于中国。
父母连同家里人都说潮州话。在唐人街,不会说泰国话没有大碍,生意人和顾客都是潮州人。不会说潮州话,反而影响生意。
曼谷的唐人街犹如潮州人的天下。泰国社会对不断涌入的中国移民十分宽容。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华侨被排斥,受压迫。但泰国没有,或许是信奉佛教使泰国人更包容、善良。
我的幼儿时代,泰国和平安宁,泰国以外则战火连天。日本将战线一路推到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父亲一帆风顺的事业也笼罩上了乌云。
-4-
母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在曼谷开了“正大庄”种子店,大本营还是在潮州老家汕头。汕头农场培育的菜种经香港,销往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父亲的种子只要是热带气候都能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切断了从泰国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泰国和中国的往来被阻断后,父亲没有安安静静地待在泰国,而是去了马来西亚的分店。那时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父亲去后被困无法出境,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返泰国。在成都上学的大哥谢正民和二哥谢大民被困在中国。日军进驻泰国前,泰国政府与日本缔结日泰攻守同盟条约,躲过了战火。那段期间,曼谷的店铺只能交给三叔谢少飞代为打理。
父亲很少待在曼谷。我的童年回忆几乎都是与母亲陈金枝连在一起的。每到饭点,母亲就对佣人们说:“你们已把饭菜准备好了,我饿了,你们也一定饿了。现在没什么活了,你们也去吃饭吧。”母亲温柔亲切的声音,一直在我幼小的耳边萦绕。我的外公也是潮州人,家里是经商的,生意做得很大,但一场罕见的灾害让他们家破人亡。

(谢国民先生的母亲)
母亲小的时候潮州发生过海啸,死伤无数。母亲家靠近海边,被海水冲走了所有家当,家里破产了。我的外婆不幸遇难,有兄弟姐妹虽幸运逃过一劫,却不得不靠讨饭生存。我的外公也逃到了曼谷。
也因为这个关系,母亲从不忘记扶弱济困,很同情和照顾贫寒的亲戚,每周都会给他们送些钱过去。母亲的钱几乎全都用于接济他人了。母亲对周围的人讲:“钱不重要,孩子们才是我的财产”。母亲过世时,不只是亲戚,佣人和司机也都哭得很凄凉,因为母亲生前一直都把他们当作家里人照顾。
也许是富有同情心,也许是善解人意,母亲总是雪中送炭。得到帮助的人日后总会来报答。其实就算没有回报,母亲也毫不在意。
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给予”,这也是公司经营的立足之本。经营者一定要将心比心,懂得换位思考,给予员工和客户机会或利益。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人生哲学。在之后的岁月里,因忙于工作,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甚少,这令我至今追悔莫及。
-5-
儿时的梦想——当电影导演
做梦也没想过长大后会当企业家。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电影导演。我痴迷香港电影,爱看文艺片和动作片。我照着电影剧本试着学写自己的剧本,还在学校舞台上为老师同学们上演过自己编排的剧目。
我还迷上了魔术。那时没有电视,第一次看魔术是在一场演出里。我让魔术师教我怎么变,回家后勤加练习。我学会了从箱子里变出鸽子,还能让空罐子里涌出大米。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是华侨在曼谷开办的学校,上课基本用泰语,每天会有一个小时的中文课。一年后,我转到位于曼谷西边万磅县的教会寄宿学校,那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日常生活都得靠自己。同学大多来自富裕家庭,有的甚至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学校里华侨子女很多,但不教中文,只用泰语上课。中文学习的中断让我在日后学习汉字上吃了不少苦头。
平时的娱乐只有锻炼身体。学校每周有一次泰拳课。班级之间打架,通常是用泰拳一决胜负。

(谢国民先生(前排左三))
我从小喜欢照顾小动物,9岁开始养斗鸡和赛鸽。因为是寄宿学校,无法自己养,就寄养在老师家里。我现在仍然喜欢斗鸡,时不时会去看上几场。
太平洋战争期间,父亲被困在马来西亚,战争结束后才返回泰国。在泰国没过多久,父亲又去了汕头。除曼谷“正大”种子店外,父亲在汕头还有一家叫“光大”的公司,从那里出口菜种。父亲在汕头农场专心改良品种。
1945年8月,二战以日本投降而告终。中国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内战。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赢得胜利,1949年10月,共产党宣布成立新中国。共产党刚上台时,父亲所在的汕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新政府执政初期推行灵活的经济政策,探索公私合营、共存共荣的道路。不但没有排斥父亲这样的私人企业家,还呼吁全世界的华侨回来建设祖国。潮州出身的华人华侨也纷纷将子女送回家乡。
我欣然接受了父亲的提议,自愿报名去汕头学习。那时我11岁。
-6-
回到汕头 苦学汉字
11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我乘大型客轮,从泰国曼谷出发前往广东汕头,这也是我第一次坐船。船在风浪中不停摇摆,很多人晕船,但我没有晕船。一周后,客轮抵达了父亲所在的汕头。
父亲的故乡澄海蓬中村隶属汕头市。在蓬中村和汕头的旧市街,父亲都有房子。汕头作为通商口岸,建筑风格早年受到西方影响。街中鳞比的“骑楼”建筑群,吸取西洋外廊式手法,将底层屋檐部分拓展出来,毗连串通成沿街走廊,形成遮阳避雨的行人通道,成为汕头的一个独特街景。我住过的房间在骑楼式建筑的三楼。房子现在还在,早已无人居住。那时,父亲常常不在家,几乎都在农场。我在汕头生活,没有语言障碍,因为在曼谷家中我跟母亲讲的就是潮州话。
我的最大问题是不识汉字。我只在曼谷念的第一所小学学过一年中文,之后的寄宿学校都是用泰语教课。1952年,我在汕头插班上了小学四年级,汉字必须从头开始学。
当时的小学,即便是同班,同学间的年龄也相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未上过学的大龄同学和海外归来的华侨子弟被分到一起。我的年龄在班里虽然有些大,不过还不是最大的,班里还有年过15的同学。
为了不被同学嘲笑,我开始苦学汉字。我从书店买来潮汕字典,从同学那里借来一年级、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放学后在家自学。我喜欢晨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后,会在自家的阳台上背记汉字。学校几乎天天有考试,每次考完语文,我都请老师给我再做一次讲评。
中国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发音和语法差别很大,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教育。我的小学校里每个星期也会有一次国语(普通话)课,但我学得并不理想,说得也不流利。后来在台湾投资做生意才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国语。

(在汕头上小学的谢国民先生)
进入五年级,我的名次升到第二、第三。认识汉字后,学习也轻松了许多。算数是我的得意科目,不用学也能够考高分。学习成绩的提高,让我有时间重新开始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泰国上小学时,我就喜欢斗鸡,于是我又养起了公鸡,还经常把自己养的鸡拿去挑战周围邻居的鸡。
我还从父亲农场拿回良种鸡苗,养起了母鸡。班里同学也轮流来家里给母鸡喂食。母鸡下了蛋我就分给同学带回家。在我家的晒台上有一个大鸟笼,里面有几十只大白鸽。我每天喂养鸽子,对鸽子进行放飞训练。记得有一次我放出去的鸽子中有几只没能回归鸟笼。我找到一个养鸽子的少年能手,向他请教养鸽子的秘诀。多年后我从事家禽饲养方面的事业,或许跟我童年养鸡养鸽子有关。
照相机在那个时代还很稀罕。我迷上了照相机,经常用父亲的相机给老师和同学们拍照。有时还会使用自拍按钮。照片都是自己在家冲洗。每次都把冲洗好的照片分送给大家。我喜欢新机械和新技术的性格,让我日后的事业受益匪浅。
▼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图·文》来源于互联网及用户投稿,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若有侵权或其他,请联系我们微信号:863274087,我们会第一时间配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