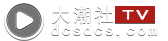郭小东:从大潮汕写“中国往事”五卷本 ——五卷本写作余笔
▼
国际潮青联合会将聚焦全球不同领域和行业中有影响力和创新力的潮商和潮青,为全球潮青构建合作发展平台。

郭小东,1951年生,广东汕头潮阳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科二级教授、一级作家、申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聘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第八届广东省政协委员。首届“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被授予“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称号、曾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突出贡献奖、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广东省鲁迅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主要作品有《中国知青部落》《中国知青文学史稿》《铜钵盂》五部,《郭小东文集》等六十余部。
在教学之余,用五年时间,写完“中国往事”五卷本:《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桃花渡》(《1966的獒》)《十里红妆》。写完了,出版了。余笔未尽。对于大潮汕的书写,似乎刚刚开始。五部长篇小说,一百八十万字,叙事与呈现,包括说辞,仅是大潮汕当代文学的零头。许多社会与人文话题,也还未入当代作家的文学视野。大潮汕的文化宽域,旷野无涯。单是潮汕女性,千年都写不尽。何况!
本已言封笔,但若余生宽富,将笔力以赴。
从溪东到中鞍头,其实是很短的距离,却要经练江、榕江、湖泊、海边湿地、平原和多石的海岸,无端隆起的丘陵,辽阔的田洋,多座15世纪的教堂和文艺复兴以后的碉楼。无论向南,或向东,尽管方向稍偏,但距离大致相等。再往前,就是大海。去大海的起点,或生命的终点,有两个:一个是有栈桥和寮居的中鞍头;一个是有薯郎牛血渗透的拍索埕。许多人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两个地方。
人一走进这两个地方,故事就有了结局,一个重归往生,一个去向未来!
在某个下雨的黄昏,火烧云在天际,半藏在海中。“雨来噢!”雅姿娘在海岸上站成一个剪影,丰乳肥臀,有红色的毛边,而衣裾飘扬部分,却是透明的海的晚风,有黑色的波浪在忧伤中流动。
繁华然而虚弱得慵懒,同时变态成痨病症的城市,呼吸里有太多的空洞,像乡下的风箱在抽。
有堤岸的地方,基本上是涂抹着粉黛的呻吟与喘息,总是在夜里过分放纵而透支了风华,早晨入睡时已成一副空壳,天亮正是它黑夜的开始。
这部自《铜钵盂》《仁记巷》《光德里》,从这些流光溢彩,却苦难深重的屋厝写起,而坠入《桃花渡》,渴望《十里红妆》去的五卷本长篇小说,它无奈地走过田中央,这个百年前潮汕“七日红”的圆点。它们中经溪东,与陈公河一起,藏宝八百年而终成废墟。
它在龟头海拐角,去龟山和蛇山,以南渡下尾河东,再见中鞍头寮居。小小的拍索埕,只不过是,风吹过隙时,鬼头刀下,一丝凉凉的血痕。
所以,小说应该拥有一个花篮,叫青篮。装满库司和香烛,金银两种,红白两种,焚之通神,三奇而多奇。
经过南门李,抬头见“李氏家庙”,差点忽略一座明正统年间已阅三世,四世的古坟……宛容安在。
在广澳角的古驿道,想起“沉东京浮南澳”的神话,以及四个小鬼搬龟山填门嘴的诡局。在佩服江西小神仙的同时,还是要感念另类半面神的神机妙算。否则,怎么会有同治元年潮阳“发财公”的传说,以及郭范两家“德盛土行”的百年神话。当然,曾国藩拿不到土行军饷,太平天国只好席卷中华。天京百世,国人静好!
从后江看过去是东湖,一个出产黄瓤西瓜的海边小村。明明是面对大海,却自称后江,非把地理上属后库的濠江,当前锋。再把一个没有河的小村,佯称河渡,然后,拍出电影《无名岛》。这就是青篮,一个装得下所有所说的地方!
还是有荒凉的地方,起码它容得下真实真相。在无人的海岬下尾,才真的是诗与远方。
小提琴和小号,在无名的风中吹响!只有曼妙的音乐,无标题,无言语。唯有不知,不说,任由流淌的荒凉,才真的值得生命为之付出。凡是明确正确,光荣伟大,都与生命、与音乐无关。如是,也将是。
写过同治,中经己丑,结于己亥。一百五十年间,五代人的潮汕,蚀骨融髓的人情风土,就这样。
无数平淡的生命和岁月,在潮汕歌册里,几声轻唱,几段锯弦,几下胜杯(掷卦),再把万千“库司”,焚为一缕青烟。在烟尘里,回眸细看,潮汕仍在,在有无中。苦恼的是,在《十里红妆》中,我无法确定苦初3号和光的命运。他们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在小说里,努力寻找的,不过是一份情义。至于许多与他们相似或关联的所谓真相,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也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可言。胜利者也并不能决定人性的胜败。真正真实的人间情怀,常常在失败者那儿,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出神入化。可惜这一切,遗忘与丢失,应是它们的命运。
苦初3号和光,他们像儿时的游戏——打水漂:一块块残缺的瓦片,被用力甩出,它们作为个体,贴着水面,与水面平行着跳跃,翻飞而去,把平静的池水点划出一圈又一圈大大小小的涟漪。
想像那不断扩大的涟漪,它们突破池水的局限,至大无边。
而池塘却年年如是,复为春水,了无痕迹!如有限的人生,在无限中的消失。
从田中央,从溪东出发,或经中鞍头南渡,又或在拍索埕终结……他们以青春绞断岁月,遂以生命结绳记事。
他们将时间拧挂出十里红妆的花信。由是唢呐低吹,椰胡乱马。天地间,忽然就彤红姹艳,欢喜了!
有一个声音:“那含泪播种的,必含笑获享收成。”
《圣经》的话,谁真正懂得?
然而,天堂是喜欢了!人间是欢喜了!欢喜了!到处是锣鼓声!
说是“中国往事”,无非是说说以潮汕为情怀的中国往事。常常有人问起怎样写潮汕?把潮汕当中国来写,或说把中国当潮汕来写,这就是了。潮汕乃中土,五山环侍如国中五岭,三江穿流如烟雨九派,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非也!潮汕延续且保持了中国三千年的文化血脉,即使当年,独送宋呙入瀛海,潮汕惟存,是为中原形胜地。
《十里红妆》是”中国往事”五卷本的最后一部。是父亲母亲们,在大时代的风磨里,经历碾压与风吹的,绝不平常的爱情。于我个人而言,是在大潮汕辽远的文化泥淖中,屡经跋涉之后的告别,而于大潮汕文学的中国讲述,才刚刚开始。
说是开始,关乎写作。写作不是我的专业,我始终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于我而言,写作不在谋生糊口,故不至于因此为五斗米折腰。也不必故作冬烘,更无须假装正经,穷酸斯文地以写作去为生存谋篇布局。写作本就在我人生主题之外,所以,期望无以无之。
母亲于乱世中生下我,遂送与船老大收养。三个月后,外祖母心有不甘,悄然找回。在我十五岁远行时,母亲对我的嘱咐是:“找件事做,娶个貌美如花的雅姿娘,遑论贫富,但家世要好。”如此而已。我揣着这个平实的嘱咐,到黎母山原始森林里,当伐木工,做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种,六年有多。其间虽九死一生,命乖运蹇,却也未遍体鳞伤。此后浪迹天涯,忝为人师,居然浪得平生,同时应了母亲的嘱咐。这才是我的真实,也是一个人的幸运。
因为教书,不敢怠慢学生,所以先学习写作,居然得若干虚名,几十本书。自以为透彻了世故,庶无忧伤?但文学应是另一回事,它始终在病痛中,容不得有丝毫的欢喜。否则,人们期待痊愈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因此,不断地写,不断的问题,以至于怀疑究竟何为?
某年九月至有年三月,写作《中国知青部落》及《桃花渡》时,眼见得旷野亡魂,又满山桃花里,却无风过隙,竟索然寡味。心想,若依人生形似,写作做甚!遂问:何以是苦?陈冠先生无意随囗应道:”到处是伤,到处是痛,到处在流血,却遍寻不到伤口,没有伤口,这就是了!”想不到有此一说,于困惑中豁然,如坠朗朗中也。自此,写作有了起色,不敢说百里穿杨,但屡屡命中,在启应中。又见《箜篌引》附之自识:“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明人祝允明尚且如此。又五百年逝去,知者谁呢?惟有不知,方解中国语文之惑。
不知当下作家,是否大多惑离中国语文常识常理,故写猫画虎,虽纤毫毛细,仍不知风在哪里?因风不可形就,故无风叶满山。
为中国作家而怯陌于中国语文,特别是缺失中古文言的浸淫,这是现代汉语写作的病源之一。五四作家,人人天生有两套语文,是故文学大师云集。有一点可以讨论的是,中国语文在发展过程中,受暴戾污染的程度不可忽视。自谓体会殊深。余从小学到初中,老师大多是民国遗老,留过洋的。大学时期的老师及文坛长辈,均于民国受完学业。人在文白双授之中,稍加努力就可圆通文章,是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语文基础,不是吗?现在的学子,没这种福份。连导师都是文革后,语词风骨缺少文白的焠炼,自然就没了那般典雅的风度。老语文已早早退场,新语文便没了源泉!
故有些事,真乃不知有汉。
▼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图·文》来源于互联网及用户投稿,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若有侵权或其他,请联系我们微信号:863274087,我们会第一时间配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