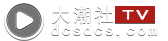潮汕话|潮汕方言“鹞婆叼鸡囝”
▼
儿时在农村常听大人吩咐,要提防“鹞婆叼鸡囝”。“婆”潮语读作“波5”,就是“姑婆”的“婆”。我好纳闷:为何要提防的是“鹞婆”,而不是“鹞公”?心想“鹞公”比“鹞婆”更凶才对呀!后来大人又说:“鹞婆有母的,也有公的。”于是追问:“既然叫婆,怎么是公的?”大人指着墙角的大竹篓反问:“笚(读卡4)婆是母的?”对呀,笚婆就是装鱼虾的大竹篓,何来公母呢?再后来,我又见到了被称作“蚝婆”,难分公母的大牡蛎。
儿时在农村常听大人吩咐,要提防“鹞婆叼鸡囝”。“婆”潮语读作“波5”,就是“姑婆”的“婆”。我好纳闷:为何要提防的是“鹞婆”,而不是“鹞公”?心想“鹞公”比“鹞婆”更凶才对呀!后来大人又说:“鹞婆有母的,也有公的。”于是追问:“既然叫婆,怎么是公的?”大人指着墙角的大竹篓反问:“笚(读卡4)婆是母的?”对呀,笚婆就是装鱼虾的大竹篓,何来公母呢?再后来,我又见到了被称作“蚝婆”,难分公母的大牡蛎。
我终于明白,“鹞婆”“笚婆”“蚝婆”的“婆”与性别无关。
普通话里“刀子”“碟子”“房子”“车子”“胖子”“二流子”,这些“子”字不能看作是孩子、儿子的意思。至于“老师”“老天”“老虎”“老鼠”这一类,有一副诙谐的对联“鼠无大小皆称老,鹦有雌雄尽叫哥”告诉我们,“老”字与年龄无关,不能望文生义。
这一类词,由表示具体词汇意义的语素和一个表示某种附加意义的语素组成。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叫作词缀。像“老师”“小王”“第三”的前一字叫前缀,“刀子”“花儿”“党性”的后一字叫后缀。
潮州话也有一些独特的词缀。与“婆婆”“阿婆”“老婆”“老太婆”的“婆”不同,“鹞婆”“笚婆”“蚝婆”的这个“婆”,也是一个词缀,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当然,它包含的附加意义与实词的意义还有一定关联,可以看作从“辈分大”含义引申出“体量大”这个附加意义。“公”“母”两字也有这个用法,如:碗公、骹公、姜母、药母、拳头母,等。
再看“鸡囝”,指的是小鸡。这个“囝”字也是词缀,读作“京2”。潮州话的“囝”作名词指孩子、儿子,虚化为词缀表示人或物个儿小、数量少,如:椅囝、鼎囝、姐弟囝、一撮囝,或轻蔑称某类人,如:刺囝、鼠贼囝、日本囝。顺带说一下,“囝”这个字,被很多人误写成“仔”了。其实“仔”字原本没有“京2”读音。因为是“崽”的异体字,后来被训读为“京2”。
潮州话词缀以后缀为主。再看看几个常见的例子。用“伯”“婆”(读破5)分别表示某类不喜欢的男人、女人:大食伯、老实伯、恶婆、媒人婆。用“头”表示特定的地方、时间:灶头、眠起早头,也可指某些人和东西:刺头、豆头、家伙头。用“鬼”表示贬损、讽刺的人:咸涩鬼、臭聋鬼,有时带亲昵色彩:贪食鬼、奴囝鬼。这些名词的后缀也都是从名词虚化而来,不能简单按原来的含义去理解。“刺头”和“刺囝”都可指刺儿头、小流氓,“头”和“囝”并无区别。
带相同词缀的一类词具有共同的特点,词缀就成了这一类词的标志。如:阿姐、阿强、阿福叔、阿卖水果,这些词用前缀“阿”打头,都是表示人的名词,“阿卖水果”就是“那个卖水果的人”。有一位朋友名叫“镇伟”,用普通话说易被误为“镇党委”,但在潮州话口语中却从不混淆,因为大家都叫他“阿镇伟”。“阿”就是人名的标志。本栏9月份拙文讲到“揭阳伙”的“伙”字,意为“某个地方的人”,读近似第三声“化”。这个字还演变、发展成词缀,放在称谓词的后面,表示“某一类人”,读音也是“化”。如后生伙(后读校)、头脑伙(领导们,脑读颗)、妈人伙(女人们)。
还有一个有趣的规律,潮州话名词后缀的前身,即虚化前的名词,多与人有关。你看,“公”“婆”“母”“伯”是人的称谓,“囝”本义是子女(如今的口语还有“医师囝”“头脑囝”之说),“头”更是人身体的部位,“鬼”与人对举,传统意识认为是人死后所变。这个规律里面可能包含更深的文化机理,有待挖掘、研究。
在合成词的结构类型上,潮州方言与普通话基本相同。“鹞婆”“鸡囝”属于附加式,“米桶”“番车”“攲重肩”等属偏正式,“店铺”“行徛”“横直”属并列(联合)式,“撑船”“镇位”属动宾(述宾)式,“食饱”“饲大”属补充式,“目涩”“日暗”属主谓式。这些都是普通话里具备的。上个月文章讲到的“鸡母”“人客”可看作偏正式合成词,只是语序与普通话相反。
2018年发的一篇谈象声词的短文其实也涉及构词方式问题。潮州话的象声词,大都带后缀“叫”,如“沙一叫”“沙沙叫”。其中,“沙沙叫”又可产生两种变体:“咝沙叫”“咝沙啦叫”。这其实是通过有规律的音节变化来构造新词。
▼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图·文》来源于互联网及用户投稿,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若有侵权或其他,请联系我们微信号:863274087,我们会第一时间配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