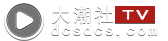平路:孩子长大后,我最喜欢的就是把他们当朋友
▼

作家平路的作品,总让人勇敢地面对社会里那些众人习以为常,却隐而不显的权力关系。谈及“十八岁公民权”,平路说:“我们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贤,其实充满年龄歧视。”
作家平路一辈子都在对抗台湾文化中的“父权结构”,举凡她的评论、报导,甚至是她的小说,都书写出在社会里隐而不显,却又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但当她听到《今周刊》民调的结果,终究也忍不住轻呼了一声:“天啊!”
毕竟,在这份民调中,不支持政府赋予年满十八岁年轻人公民权的声音,明明白白地以四七%压过支持者的三七.六%。人们对年轻人的不信任,有时候就像膝关节反射,已经成了直觉式的反应。
即使台湾的投票年龄限制老早就跟不上世界潮流,年轻人还必须忍受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对于降低投票年龄的问题,多数反对者依旧想都不必想,就能投下反对票,“十八岁的青年思想未臻成熟”这种观念,像是天经地义的事。
君臣父子观念依旧 位阶高低,却变成说理基础
平路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文化看似敬老尊贤,其实充满年龄歧视。”她很清楚,“十八岁公民权”绝对不单单是件“政治”上的事,更是件“文化”上的事。
在体制上,“投票年龄”或许还有翻转的机会,但那些文化里“论资排辈”的伦理结构,却坚决地几乎不可撼动,盘根错节虬在集体意识的深土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很多元,每个人都说台湾的问题就是太自由了,但其实可能并非如此。”
“这样的伦理结构在我们心里发声,即使没有直接听见,我们还是活在其中。”平路谈到“文化”,态度总是谨慎,每次论述前,都会沉吟再三,她很小心地又谈了下去。
“在我们的社会,‘伦理结构’是界定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据……,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在社会中会很轻易地产生某种‘权力关系’,年长者就是父权社会的根基吧!”每个人都因为年龄,有了一个社会上的伦理位置,她说:“我们不自知地活在集体潜意识里。”
“在社会上,常常可见到年长者因为年纪,变成‘伯伯’,不然就变成‘爷爷’,仿佛拥有这个身分就安定了……。作为伯伯,他是父辈阶层,年高就自动德劭,有了上对下的位置。”平路轻叹口气,“原本讨论事情,就应该要说道理,但位置的高低,却变成说理的基础。”
平路很认同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想法,这种权力规范,就像毛细管,在社会各处无所不在。
“教育体系、司法体系、公务员体系,上对下的位置都是必须‘坚守’的。”现在是司改会成员的她举例,“司法体系为何让人诟病?因为法律,人要嘛是同门、要嘛是同辈、要嘛有师承,所以即使经过一审、二审,都不会去推翻前面(那些同门、同辈、师承关系)的认定。”如此一来,人治和自由心证就取代了法治。
这种“位阶”在婚礼或日常生活中,更加显而易见,平路举例:“只要参加任何一个婚礼,你就会立刻看到,原本只是夫妻两个人的决定,却连结到多少父母的亲友,而这样的场合,传递著怎样的讯息?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个人的选择,受制于社会的伦理架构,甚至为伦理架构服务、传声。
“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在文化里。”平路认为,台湾社会至今仍保有中国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权‘维稳’的方式。”藉著这种价值观,政权得以建立起一个安稳的同心圆,下对上有一种服从关系,社会相对稳定,位置却是不能翻转的。
“长大”就能解套?打破威权,尊重应是相互的
“就像社会上,只要有年轻人与长辈冲突的新闻,年轻人就常常被冠上‘逆’。”平路说,“所有人不顾双方发生什么事,直接作价值判断。”“逆子”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是有罪的,年轻一辈的声带,也就这么被打了个结,除了服从体制,很难有任何对抗的手段。
最容易的解套办法,可能就是“长大”,这里的“长大”指的是生理年龄,而不是心智。
平路认为,“文化是非常强大的。”只要进入“伦理结构”,“社会化”的需求很快就会改变年轻人原本的价值体系,“你在社会中,要存活、要温饱,就更容易接受社会既有的规范,必须去大幅度转换认知系统,否则认知会失调,最后就会认同:‘对啊!我十几岁时其实不懂事!没有现在那么成熟。’”
“我们的社会化太早开始了,无论何时,都被规范、规劝,甚至被惩戒。”平路说,“回到结构中,就会拥有一种安全感。我们社会更努力告诉年轻人,要顺应上一代,桌子旁边就会掉下一堆好处。”
平路叹了口气又说:“对我来说,‘成熟’不是服从,而是听到自己的声音,做真正符合你心里的愿望的事情。然而我们的社会却正好相反,刚好要求人们不要去‘听见’自己的声音,听不见、漠然,才拥有所谓‘竞争力’。”文化中的“年龄歧视”、“伦理结构”,都被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牵引,年轻一辈的声音,愈来愈小声,“父权”也得以维系它牢不可破的规范力量。
欣慰儿女为梦而活 “我怎么能不崇拜他们?”
“尊重应该是‘相互的’。但是现实中不是这样,因为有了相互性,父子君臣结构会不稳。”平路苦笑。自己也从“威权教育”成长走来,她如今早是人母,“我自己成长环境比较威权,那我就是反其道而行,在一般人的眼光里,我是个太没有‘主义’的母亲,我非常崇拜我儿子女儿!”
谈到作为一个母亲,平路整张脸都亮了起来。她儿子原本在美国当律师,收入丰厚,“但他做一年律师就不做了,再也不上班了。回到台湾拍摄微电影、影像。”他现在正在拍摄一对同志伴侣的纪录片,“虽然辛苦,但是却很快乐!他业馀还做瑜伽老师!”
她女儿原本在波音公司工作,但为了实践理念,到美国新移民区域当小学老师,“所以你说我怎么不崇拜他们?”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他们长大后,和他们成为朋友,那是生命经验最有沟通的时刻,就是两个人,完全是平等的两个人,我们所交换的是,对生命经验的想法,这中间并不因为我养育他们长大,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平路笑说:“亲情,放置到伦理之外的定义,最合适的语言就是友情,因为了解、因为相知,那个基础,跟一般朋友是一样的!”
在“伦理”关系之外,社会需要的可能是更“纯粹”的沟通,平路说:“纪伯伦有首诗写,‘父母是弓,儿女是射往远方的箭’,一旦射出去,他会飞向自己的方向。”
文化设定了弹道,但相互尊重却可能融化长幼尊卑的硬壳,忘了“天地君臣父子”,记起“人”是怎么一回事。
平路
出生:1953年
现职:作家、司改会委员
经历:香港光华文化与新闻中心主任、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顾问
学历:美国爱荷华大学统计学硕士
▼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图·文》来源于互联网及用户投稿,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若有侵权或其他,请联系我们微信号:863274087,我们会第一时间配合删除。